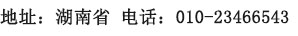4
吆喝中的老昆明昆明好玩在老昆明的街巷中,小贩的叫卖可谓家喻户晓了。记得当时那些小商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价格极低,销售的方式和今天是大不一样的,打竹板的,敲铜锣的都有,为数不少的还是沿街叫卖。其声调的高低,节奏的疾徐。各具特色:高昂者如飞瀑泻地之迅猛;低沉者如白云出岫之舒缓。从早到晚,从春到冬,它们组成了一首老昆明的都市叫卖交响曲。
在那朝阳晨风中,在那夕阳鸦噪时,从僻静的老街古巷里不时地传出一两声野韵悠悠的长声叫卖。老昆明人一听便知道是卖什么的来了。遇到挑担子卖小吃的来了,一声叫卖,嘴馋的大人和娃娃们更是会赶忙跑出来,围在担子旁边,或蹲或站地吃着,买主边吃边和卖主闲聊着,问讯着,那种随和悠闲的韵味,一直会弥漫到了深夜。它是老昆明人生活中的一道风景,一个图像,一种民俗。
每天,天刚亮,就从远处飘来了一阵阵拖着长长声音的叫卖:“白糖……凉糕……太……平糕!”随着这婉转动听的叫声传来,只见衣着干净的女人身挎木盘,边唱边走,她们那娇嫩的卖货声,带着昨夜春雨的清丽和古城的清风,一声声是那么的甜润。那木盘里放满了白糖凉糕和太平糕,买糕的人很多,尤其对开店铺的人和卖小菜的农民来说,以糕做早点极为方便,又因经济实惠,所以很受老昆明人的欢迎。
用糯米制成的凉糕本来没什么特别,但加上蜜饯、红糖水、芝麻等辅料就变得爽滑可口了。太平糕,米和冷饭磨成米浆,加入白糖搅匀发酵,入笼蒸熟,取出晾凉。再用蜂蜜加入开水搅拌刷在糕面上。一会儿。卖水豆腐的叫卖声也随之响起了:“水豆腐,豆浆!”水豆腐有清凉的作用,拌入卤腐汁,十分爽口,而她那声音清脆、响亮,像一颗颗光滑圆润的珍珠。
“米面粑粑呢卖……!”这喊声带着山野中的土味,带着乡间那特有的实在,一般是远郊的彝族妇女背着竹篓,或拎着提箩,在街街巷巷中转悠叫卖。这种粑粑既有糯米的筋道,又有饭米的香甜,而且愈嚼味愈浓,所以很受老昆明人的欢迎。特别是娃娃们清晨上学时,从那竹箩中买上一个还有热气的米面粑粑,可算是上好的早点了。
水豆腐即是豆腐脑,*豆用水泡涨,经过磨碎过滤出豆浆,再把豆浆加入盐卤或石膏、内酯,就会凝结成非常稀软的固体。米面粑粑是用糯米和饭米混合蒸熟,放在碓窝里舂捣后,做成的粑粑,一般只有小碗口大小,不放糖也不放盐。“薄荷糖,陆荫荫(绿荫荫)呢清凉薄荷糖……!”卖糖人挑着担子,叫卖着,沿街走来。他的声音清脆、响亮,押韵而富有节奏感。这种糖是用白砂糖加薄荷汁熬制而成。
方方的一大块,中间又用刀划成若干个小方格,食用时用手一掰,一块方糖落下,放在嘴中,一股薄荷的清香直扑喉头,这种清凉解渴的消暑食品老昆明人很是喜爱。
“兰花豆,梆梆脆,越吃越有味!”直到今天,我还记得那个30多岁的汉子,紫铜色的脸,头上戴顶破草帽,布纽子的衣衫,大摆裆的裤子,脚穿一双麻草鞋,肩挑一对装满油炸兰花豆的大箩筐。走起路来,如同他的喊声一样嘎嘣干脆。他那吆喝,底气很足,余音绕梁,如*钟大吕,高亢铿然。听到他那洪亮的声音,老昆明人仿佛已在大嚼那一颗颗炸得开花,香脆而酥松,口味独到的兰花豆了。兰花豆就是把蚕豆放入水中让皮充分吸水膨胀,剥去豆皮黑线,入锅油炸,炸至水分充分蒸发为止,根据口味可适量撒拌些食盐等,口感酥、脆、香。
在众多小贩的叫卖声中。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那山里来的大嫫(大妈)了。她头顶一块阴丹蓝方帕,身穿一件长到膝盖的宽大蓝色粗布衫。下着一条大裤腿的黑布裤,腰间系一条绣花的青色围腰,围腰里兜着花椒叶,手里还端个装着小白芨的筲箕。她边走边吆喝:“小白芨……!”她的叫卖声很有特色,“小白”两字叫得很短,“芨”字拖得很长。这种叫卖声多年不变,老昆明人一听声音便想像得出叫卖大嫫(大妈)的模样来。当那长长的尾音在旧街老巷中回旋时,一些老人家便会走来买上一点小白芨。他家的娃娃咳嗽了,大人们就拿出几个,捣碎后拌上蜂蜜蒸一蒸,叫娃娃吃下去,这东西苦是苦一点,但吃上几次就不咳了。
“叮叮当,叮叮当,叮叮当当叮叮当!”这是什么声音?竟如此的悦耳,响彻昆明的大街小巷。老昆明的娃娃们一听,便知道这是卖叮叮糖的小贩来了。那小贩肩挑一对箩筐,手提一把弯刀,用小铁锤敲响小弯刀,沿街卖糖。那又白又软的糖块吃到嘴里有些粘牙,香甜可口,又不上火。老昆明还有了这样的童谣:“叮叮糖。叮叮糖,越吃越想娘。”
“有……旧衣烂衫……找来卖……!”这声音如滇戏的高腔,那“有”字一吐出,悠扬而宛转,接着“旧衣烂衫”四字急促泻出,随之戛然而止,稍作停顿后,“找来卖”三字却又像山歌调子似地一个个吐出。就像一台好戏的开篇,音韵悠长,回昧无穷。这就是老昆明城中,收买旧衣裳、旧棉絮、旧被盖小贩们的叫喊声了。这些小贩多为滇东一带的家庭妇女,她们成天走街串巷,高声吆喝,用极低的价格从老昆明人的家中收购到一些破衣烂衫,然后,经过一番浆洗,再由男人们拿到文明街夜市、福照街和如安街一带去卖。来买的人多半是昆明附近,四乡八寨或外地州县的贫苦农民。衣服虽然旧,但花钱不多.买回去勉强还能穿上一段时间。
“磨……剪子嘞……镪……菜刀!”这个声音是老昆明人最熟悉不过的了。每个磨刀匠仿佛是受过统一而专门的训练,他那叫声抑扬顿挫,节奏分明,悠扬辽远,韵味淳正。听到这个人的吆喝,老昆明人有一种亲近感,因为一日三餐,做菜煮肉,好像都离不开他。有的人家还和磨刀匠交成了朋友,定期地,磨刀匠会上门服务。
老昆明的叫卖声每天就是这样,近了,又渐渐地远了,消失在古城那温馨的夜色中。
非常有意思的是,从这些丰富多彩、五光十色的叫卖中,深谙世道的老昆明人竞能听出叫卖者的境遇、性格和买卖的兴旺与否,有的人怯生生地才开口就收了尾,不用问,这是初人道者,是个新手;有的人短促而低微的喊叫,其中包含了祈求和希冀,使你难免动了恻隐之心;有的人在那羞涩而恐慌的叫卖声中,流露出了丝丝的愁苦和无奈,令你悲天悯人;有的人一声喊出,竟是旋律,是一种古典的艺术,一种美的享受;有的人一声吼出,惊天动地,犹如炸雷,极具震撼力和穿透力,自然也破坏了老昆明人对他的防御力和抵抗力;当然,还有些叫卖应该算作是噪音了,那种急躁的,迫不及待的,声嘶力竭的嚎叫,令人烦不胜烦,落荒而逃。
老昆明城中那一声声叫卖不断,老昆明人的生活一天天地过着。叫卖声绘出了一幅市井风情图。说它是旋律也好,说它是噪音也罢,反正从这些吆喝之中,我真真切切地触摸到了老昆明人那跳动的脉搏,我实实在在地聆听到了老昆明人那生存的足音。
馋货圆滚滚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